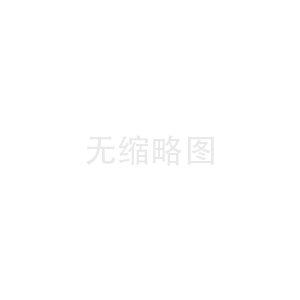老屋门楣上的“家族红”
广东广雅中学 杨之湄
我的家里珍藏着一张照片:92岁高龄的外曾祖母,坐在山东老屋的门楼下,面色祥和,静静地向远方遥望。石砌的门楼已经有些破败,门楣上有一块锈迹斑斑的暗红色铁牌,殷黄色的文字依稀可辨:“革命烈士家属”。妈妈说,这张照片就是外曾祖母后半生的缩影。
1947年,解放战争接近尾声。9月15日,外曾祖母年仅19岁的大儿子——我的大舅公,毅然参军,被编入徐向前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78师534团。
大舅公年纪小,又瘦又矮,像个孩子。当年军备物资缺乏,大舅公临走的时候连支枪都没有发,扛着一把铁锹便跟随大部队奔赴山西。当时,临汾城虽已是孤城,却被国民党经营成了“铜墙铁壁”,固若金汤。1948年2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一万多人的先遣部队,准备强攻临汾东关,开辟登城突破口,大舅公就在其中。后来,与大舅一同参军活着回来的老乡带回消息:强攻东关前夕,部队给战士们每人发了两个白面大馒头和一块拳头大的红烧肉。大舅公一手拿着两个馒头,一手举着插着红烧肉的筷子,对他说:“老郑,明天轮到我去打临汾,你要是能回老家,跟我老娘带个信儿,就说我回不去了。”
从此,大舅公再无音讯。
1952年,当年一起参军的老乡都陆续有了消息:挂了彩的,养伤复员后回来记了功;牺牲了的,部队派人来郑重地颁发了烈属证。可是,大舅公却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于是,外曾祖母便拖着一双小脚,踏上了寻子之路。
两年间,外曾祖母去了胶南县,去了青岛市,去了济南军区,最后她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山西省临汾市烈士陵园。放眼望去,一尺见长的小牌牌密密麻麻地插满了小山坡,在这些牌牌上,有的只写着一个姓,有的只写着一个名儿,有的就只写着出生地。
外曾祖母在烈士陵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三天,始终没有找到大舅公的牌牌。一直陪伴寻亲的部队领导对她说:“当初上战场前,战士们在自己的衣服、帽子、鞋子上全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自己的名字和籍贯,一旦牺牲,活着的战友哪怕找到一片衣物碎片儿,也能算作牺牲者的明证。” 那位领导接着说:“大娘啊,好些个战士,牺牲了连个衣服片儿都没留下,您上哪儿找去啊?回家吧!”
外曾祖母回家的时候,是胶南县的部队领导送回来的,一同送回来的,还有那块鲜红的“革命烈士家属”铭牌。部队领导将这块铭牌高高地钉挂在老家院门的门楣上,从此家族的门上多了一抹“家族红”。妈妈说,几乎每天黄昏晚饭后,外曾祖母都会在院门门楼里——这块铭牌下面坐一小会儿,静静地向村口张望。
2021年暑假,妈妈带着我,沿着外曾祖母的足迹,来到了临汾市烈士陵园。在向工作人员征询时,我们竟然在烈士名录里意外地看到了大舅公的名字:
“尤增桂(1929年8月-1948年2月),男,山东省胶南人。生前是一七八师五三四团的战士,1948年2月在临汾牺牲。”
此时,展览厅里一直在循环播放着一首歌:“在茫茫的人海里,我是哪一个?在奔腾的浪花里,我是哪一朵……山知道我,江河知道我,祖国不会忘记,不会忘记我……”
从我记事起,妈妈就经常给我讲述外曾祖母和大舅公生离死别的母子情。大舅公短暂而英勇的一生,外曾祖母平静而坚忍的后半生,让年幼的我很早就懂得了要珍惜眼前的安宁和幸福。外曾祖母是一位英雄的母亲,更是一位母亲英雄,她那张珍贵的照片,连同那块悬挂在老屋门楣上的“家族红”,永远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里。
指导老师/钟秀平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